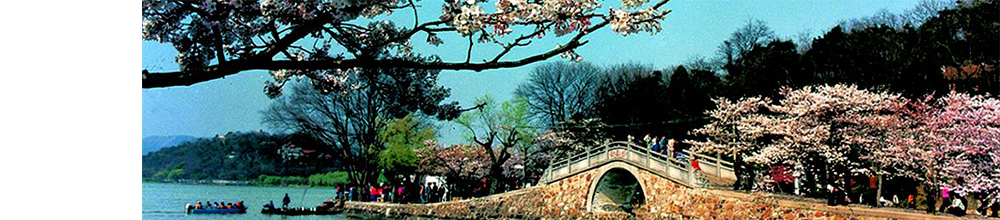【基本信息】
1.终审裁判文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锡民终字第0168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肖像权纠纷
3.当事人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陆永兴。
被告(二审上诉人):薛仲良。
【基本案情】
1999年,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为宣传需要策划出版了《冰心与江阴》一书,由薛仲良主编。薛仲良利用陆永兴与冰心的合影照片,通过图片编辑软件将陆永兴躯体部分影像保留,头部影像更换成薛仲良的头部影像,形成了薛仲良与冰心的合影照片,并将编辑后的照片刊登在《冰心与江阴》内发行。
2008年4月18日,陆永兴起诉至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薛仲良立即停止侵害他的肖像权的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并公开赔礼道歉;判令薛仲良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案件焦点】
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为个人名誉虚荣心,利用PS技术移花接木分割他人与名人的合照而公开发行,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
【裁判要旨】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肖像权保护范围不限于人的五官,还包括人的躯体。薛仲良利用陆永兴与冰心合影通过电脑技术,使用其中陆永兴的躯干影像,合成为自己与冰心的合影,该行为侵犯了陆永兴的肖像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薛仲良停止使用其利用陆永兴与冰心合影照片通过电脑技术合成的其与冰心的合影照片。
二、薛仲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在《江阴日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陆永兴赔礼道歉(具体内容由本院审定)。
三、薛仲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陆永兴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四、驳回陆永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薛仲良不服,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肖像是采用摄影或者造型艺术手段反映出来的自然人的形象,只有自然人自己才能决定对自己肖像的使用。所谓肖像权是指法律赋予自然人对自己形象再现(肖像)的排他性支配权。作为人格权,肖像权既是民事权利,更是公民基本权利。它的权能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积极作为”的“支配”属性,如肖像使用权,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另一种是“消极防御”的不受侵犯属性,如维护肖像完整权,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有维护完整性的权利,有权禁止他人非法毁损,维护自己的尊严,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社会公众一般比较重视照片中自身影像的完整性,特别是将头部与躯干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尤其忌讳将已成影像中的头部从躯干上人为地去除。且对于任何普通民众来说,能与中国知名作家冰心合影,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合影的照片亦具有珍藏价值。本案中,薛仲良未经肖像权人陆永兴的许可,擅自通过电脑技术将陆永兴视为具有特定价值的照片中的头部影像从其整体影像中分离,破坏了陆永兴肖像在该合影照片中的完整性,其行为侵害了陆永兴最基本的肖像完整展现的专有权益,已经构成侵权。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9年4月2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适用解析】
一、肖像权的民法保护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事法律对于肖像权的保护先后体现在《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的有关规范中,而《民法典》则开启了包括肖像权在内的人格权保护的新时代。《民法典》创设了人格权编,其中肖像权单独成章,内容空前丰富,条文严密,既扩展了具体人格权保护的范围,又强化了对生命尊严的保护,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学发展、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成果,对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大长远历史意义。可以说,人格权编彰显了民法的价值理念。[1]
(一)肖像的基本要素
肖像权是建立在自然人肖像基础上的权利束,要深刻理解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规范,首先应该把握肖像的基本含义。所谓肖像,《民法典》第1018条第2款规定,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根据该款规定,肖像的认定需要把握几个要素:(1)肖像反映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具有可固定化的特征,而反映肖像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影像、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能够反映自然人肖像的方式可能更加多样化、多元化。比如,3D打印技术完全可以艺术化的再现一个人的形象,该形象完全可以作为民法典保护的肖像或其他人格权。(2)肖像是自然人外部形象的再现。通常观念认为人的脸部特征具有直观的可识别性,是肖像权保护的重点,但是肖像权保护的对象是自然人形象的整体再现,其体型特征、外貌特征、声音等诸多与自然人相关的形象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反映在载体上,都应该是肖像权保护的内容,对此民法典有关规范亦有体现。(3)肖像可识别为自然人。肖像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或技术形式使自然人的整体外部形象在物质载体再现的视觉形象,肖像权保护的是自然人因肖像视觉形象产生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如果通过特定的技术或艺术反映出来的形象不能特定化,不能被识别,那么就无法确定是否侵害了特定自然人的权益,也就失去了保护的主体。
(二)肖像权的权能
人格权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认为,人格权的权能主要包括了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
1.肖像权的积极权能。《民法典》第1018条第1款规定即为肖像权积极权能,即自然人有权依法自行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具体表现为:自然人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对于自己肖像的使用,人格权编没有设立过多的限制性条款,因为这属于人格自由的范畴,法律不必设置具体的干涉条款,但法典化之后,自然人使用自己肖像的行为除了受人格权编的规范,还要受其他编以及民法典外有关规范的限制,至少有关行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侵害公共利益,不得突破行为自由的应有边界。对于肖像的许可使用,一般是通过许可合同的形式完成,对于涉及人格财产利益的合同解释和适用规则,法典人格权编第1021条、第1022条分别作了规范,即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有利解释原则和有利解除规则。将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放在了优先保护位置: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关于肖像使用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当然在有限保护人格权利益的同时,对于肖像权人无正当理由解除许可使用合同造成对方损害的,亦应当依法赔偿,据此以平衡人格利益与他人财产利益,相关规定至为合理。当然对于肖像权的许可使用,同样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正如民法典第993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
2.肖像权的消极权能,是一种防御性权能,是肖像保护的精神利益核心所在,旨在保护自然人对自己肖像使用的控制权,防止他人以不当手段破坏自己的“形象完美”,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制图软件和制图平台的技术支持使侵害者对他人肖像的制作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2]肖像可以被以移花接木的方式随意“换脸”,高科技的爆炸更加凸显了人格权益保护的重要性。[3]正是基于通常侵权的两个方面,民法典在1019条对于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二、肖像权保护的限制
正如任何权利都有相应的制约边界一样,民法典对于肖像的保护也应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无限延展。根据法律适用的体系性规则,对于肖像权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合理使用、保护期限、著作权对肖像权的限制等方面。
1.肖像权的合理使用。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了5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分别为:(1)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2)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3)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4)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5)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合理使用应以必要性为限,也就是有关组织和个人在使用他人肖像时应该以对肖像权人造成最小的不利益为限。除上述法定方式外,司法实践还在某种情形下发展了合理使用的方式,比如,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可以善意使用他人肖像;用人单位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其工作人员肖像等。[4]
2.肖像权的保护期限。民法典没有直接规定肖像权保护的期限,但是通过其他规范可以推定出肖像权是有保护期限的。首先,自然人存活期间,依法享有肖像权并主张肖像权利自不必待言;但自然人死亡后,对于死者肖像的保护却存在一定期限限制。民法典第994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民法典是通过权利行使的主体间接限制了肖像及肖像权保护的期限,因为无论是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及近亲属都是法定的人群范畴,相关人员都有自然的生命周期。当然在特定的情形下,不排除为了国家或公共利益需要对特殊人物的肖像予以更长期限的特殊保护。
3.著作权对肖像权的限制。当一项智力成果以人物肖像为素材、原型时,最终的成果融合了肖像权和著作权,肖像作品是两种权利共同的载体。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应该尊重肖像权人,不得非法侵害肖像权人利益;反之,肖像权人也不得非法侵害、限制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两者互为制约。
三、本案裁判的时代背景及超越
庞德曾指出,法律存在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的冲突,所有法律思想的目的都在于协调这种必要性与变化性。[5]司法裁判很多时候亦是两者之间协调的艺术。《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虽然从立法层面有了突破,确立了肖像权的法律保护。但具体保护却仅限于“以营利为目的”,即肖像权的财产属性,而对肖像权最基本精神利益的保护出现法律欠缺。
碍于肖像权保护立法的局限性,具体到本案的实务处理,虽然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薛仲良未经肖像权人陆永兴的许可,擅自剪接陆永兴的肖像,构成肖像权侵权,但两者判决的理由大相径庭:一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100条,从薛仲良损害的是陆永兴肖像权物质利益来阐述;二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5条法律原则,认定薛仲良损害的是陆永兴肖像权的精神利益。
为了套用“使用肖像”的概念,一审认为肖像不只局限于人的五宫,还包括人的躯体。只要具备“未经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两个要素,即使他人从剪接后的影像中无法辨别出肖像权人,也构成肖像侵权。
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所谓肖像是通过摄影、雕塑、录像、绘画、电子数字技术等手段,将自然人的五官特征、形体特征、肢体特征或其他可识别特征以物质载体或虚拟物质载体方式表现其全部或局部并能够为人们主要是通过视觉方式感知的形象。肖像是肖像人外部形象的再现,并体现肖像人的人格利益。这是法律意义上肖像构成的首要要件,否则不能称之为肖像。肖像最基本的功能是识别功能,一审法院将不具有识别特征的躯干作为肖像归类于法律保护的范畴,显然在语义上存在逻辑错误。
《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首先,肖像权作为一般人格权,具有人格权最基本的属性—精神利益,公民形象的完整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损毁、恶意玷污,这是人之所以作为人存在的最基本权利。其次,肖像权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具体权利形态,又具有其特有的属性——物质利益。虽然它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但它与人的名誉与财产密切相关,人们可以利用肖像权进行营利。综上,我们在审理肖像权案件时不应拘泥于《民法通则》第100条之规定,只要未经本人同意,无阻却违法事由擅自使用他人肖像,无论营利与否,均可认定为肖像权侵权。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法的内涵实在。随着电脑、互联网、APP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肖像权的保护内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旦肖像再现于物质载体就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整体利用或是局部利用他人肖像的目的主要为谋取经济利益。而随着IT技术的发展,通过修图软件,肖像可以轻易地与物质载体相分离,保护肖像权的法律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肖像权的财产权益,更在于它的人身属性。《民法典》第1018条、第1019条的规定,完善了肖像权的全面保护,是民法典开创人格权立法新篇章的重要内容。
[1] 王泽鉴:《中国民法典的特色及解释适用》,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3期。
[2] 谭子恒,周熙莹:《互联网时代肖像权的保护》,载《传播与版权》2019年第5期。
[3] 王利明:《人格权法的新发展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4] 张红:《民法典之肖像权立法论》,载《学术研究》2019年第9期。
[5] 罗科斯·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